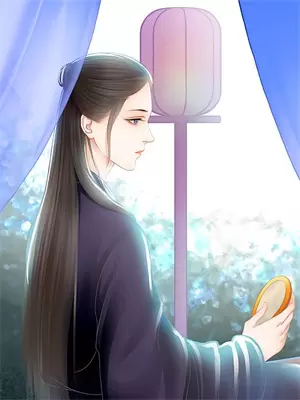警察上门的那一刻,我妻子正蜷缩在沙发上发抖。而我的口袋里,
揣着那块从车祸现场捡来的、属于肇事车辆的车灯碎片。警察问我:周老师,
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?我看着妻子惨白的脸,平静地摇了摇头:没有。
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谎言,它像一颗子弹,将我的人生射向了无法回头的深渊。
1世界是在我家车库里崩塌的。没有巨响,只有一块塑料碎片嵌合的轻微咔哒声。
我从ICU回来,身上还带着消毒水的味道。儿子小远还躺在里面,身上插满了管子,
呼吸机代替了他的肺。医生说,能不能醒来,看天意。警察来过又走了,他们勘察了现场,
说肇事者逃逸,现场很混乱,暂时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。可他们不知道,有一块线索,
一直被我死死攥在口袋里。我冲到小远身边时,
我的世界只剩下他微弱的呼吸声和满目的鲜红。混乱中,我的手在地上胡乱地抓着,
似乎想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。然后,这块冰冷、锋利的塑料就嵌进了我的掌心。
救护车呼啸而来,警察拉起警戒线的时候,我甚至忘了它的存在,
它就静静地躺在我的口袋里。直到此刻,回到家,我才在洗手时,从口袋里掏出它。
借着灯光,我才看清,是一块车灯的碎片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进车库。
也许是潜意识在牵引。老婆的车就停在那里。我走过去,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
我的心跳得像要炸开,耳边是ICU里单调的滴、滴声。右侧车灯的位置,
有一处崭新的破损。一个小缺口,像一张怪笑着的嘴。我的手在抖,
几乎握不住那块小小的碎片。我闭上眼,把它凑了过去。咔哒。天丝合缝。那一瞬间,
我听不见任何声音了。车库里的灯光、远处的犬吠、我自己的心跳……全都消失了。
周峰……妻子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,很轻。我僵硬地回头。李月穿着单薄的睡衣,
站在车库门口。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白得像纸,头发凌乱,眼神空洞。
她看到了我手里的碎片,看到了车上的缺口。她什么都明白了。她没有说话,没有哭喊,
甚至没有摇头。只是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,然后,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滚落,
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,无声无息。我看着她,脑子里只剩下两个选择。报警。
我唯一的儿子还在ICU生死未卜,我的妻子,将被戴上手铐,坐牢。这个家,会彻底完了。
或者,把这个秘密,连同那块碎片,一起吞进肚子里。让它在我的五脏六腑里腐烂、发臭,
直到我死。我该怎么办?2门铃响的时候,李月像只受惊的鸟,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,
抓住我的手臂,指甲深深陷进我的肉里。是……是不是警察?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
我拍了拍她的手背。别怕,我去开。我用了毕生的力气,
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还算镇定。门外站着两名警察,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,姓王,
另一个是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,姓刘。周老师,打扰了,我们想再了解一下情况。
王警官的语气很沉稳。我把他们让进屋里,客厅里一片狼藉,妻子的包倒在地上,
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。我请他们坐下,自己却站着,仿佛这样能给我多一点力量。
李月蜷缩在沙发的角落,把脸埋在膝盖里,像是在惩罚自己,又像是在躲避这个世界。
周老师,小刘警官打开了记录本,您再仔细回忆一下,在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?
比如车辆的颜色、型号,或者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?我的口袋里,
那块塑料碎片硌得我生疼。它像一个邪恶的魔鬼,在我耳边低语:说出来,
说出来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我看向李月。她瘦削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。我无法想象,
如果我说出真相,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。小远还在医院里,如果他醒来,发现妈妈进了监狱,
他会怎么想?这个世界对他来说,会变成什么样子?我的喉咙像是被水泥堵住了,
每一个字都说得无比艰难。没有。我说。现场太黑,太乱了。我……我只顾着看孩子,
脑子里一片空白,什么都没注意,什么都没听到。第一个谎言,像一颗子弹,
从我的嘴里射出。没有回头路了。王警官看着我,眼神锐利,似乎想穿透我的身体,
看到我藏在口袋里的那个秘密。他沉默了几秒,然后叹了口气,转向蜷缩的李月。
这位是……嫂子吧?您别太难过了,身体要紧。您出事的时候在哪里?
有没有可能看到或者听到什么?李月猛地抬起头,满是泪痕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绝望。
她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我抢先一步开口。她当时在家,接到我电话才赶过去的。
她……她吓坏了。我走过去,将妻子搂在怀里,她的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。
小刘警官合上本子,站起身。周老师,您也别太难过了。你放心,
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抓住凶手,给你和孩子一个交代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那句充满正义感的安慰,像一根烧红的铁钎,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。
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谢谢……谢谢你们。送走警察,我关上门,
背靠着冰冷的门板,整个人像被抽空了骨头,缓缓滑坐在地上。李月扑过来,跪在我面前,
抓着我的裤腿,终于哭出了声。周峰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我对不起小远……我没有说话,
只是从口袋里,掏出了那块要了我们全家命的碎片。然后,当着她的面,
我把它紧紧攥在手心,感受着那锋利的边缘,再次割破我的皮肤。用疼痛,
来铭记这第一个谎言的味道。3钱,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流走。
ICU的账单每天都像一座山一样压过来。我拿出了所有积蓄,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,
才勉强维持着。小远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。我白天是周老师,在课堂上强撑着笑脸,
给学生们讲鲁迅,讲真的猛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。可我自己,
却连直面现实的勇气都没有。晚上,我是悲伤的父亲,守在ICU外冰冷的长椅上,
透过一小块玻璃,看着那个被仪器包围的小小身影。李月不再去医院了。她害怕,
她说她一看到小远,就感觉自己快要死掉了。她把自己关在家里,日渐消瘦,
像一朵正在迅速枯萎的花。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,家里安静得可怕。偶尔的对视,
也充满了躲闪和无法言说的痛苦。那个秘密,像一堵无形的墙,把我们隔在两个世界。
学校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同情我,给我减了课,让我多些时间去医院。可我最怕的,
就是时间多。只要一闲下来,那块车灯碎片就会在我脑海里闪现,妻子的哭声,
儿子的血,警察的承诺……所有的一切都交织成一张网,把我勒得喘不过气。终于,
我还是走到了那一步。我开始在网上发帖求助。我把小远的照片,
那些他健康活泼、笑容灿烂的照片,一张张贴上去。然后,用最克制也最痛苦的文字,
描述我们的遭遇。我叫周峰,一名普通的高中老师。我的儿子周远,7岁,
于11月15日晚遭遇车祸,至今昏迷不醒。肇事者逃逸,恳请社会各界好心人,
如有任何线索,请与我联系,必有重谢。我不敢去看评论,
不敢去看那些同情的、愤怒的、祝福的留言。因为我知道,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。
我一边渴望着线索,因为只有抓到凶手,这个家才能得到喘息。我又一边恐惧着线索,
因为真正的凶手,就睡在我的枕边。我的帖子很快被本地的自媒体转发,然后,
一个电话打了进来。您好,是周峰周老师吗?我是市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记者,我叫肖然。
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年轻,充满活力和正义感。周老师,我们看到了您的求助,
非常同情您的遭遇。我们想给您做一期专访,让更多人关注这件事,帮您一起寻找真凶,
您看可以吗?我握着手机,手心全是汗。我成了媒体眼中的悲情英雄,
一个为了儿子、为了正义,四处奔走的坚毅父亲。他们要把我架到聚光灯下。可他们不知道,
灯光越亮,影子就越黑暗。我张了张嘴,想拒绝。但话到嘴边,却变成了:好,谢谢你,
肖记者。因为我需要钱,小远的治疗,一天都不能停。我也需要一个凶手,
来结束这场无休止的折磨。哪怕,这个凶手是我亲手制造出来的。
4肖然比我想象的还要雷厉风行。第二天一早,她就带着摄像师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
人很年轻,扎着马尾,眼神清澈而坚定,看我的时候,充满了未经世事的同情。周老师,
您别紧张,我们就随便聊聊。她试图让我放松。可我怎么可能放松。
摄像机黑洞洞的镜头对着我,像一只审视的眼睛。我不得不再次开始我的表演。
我讲述着我和小远的日常。每说一句,我的心就被刺一下。李月把自己锁在卧室里,
任凭我怎么敲门都不出来。我只能对肖然解释,她因为伤心过度,无法面对镜头。
肖然表示理解,眼神里的同情又多了几分。采访播出后,反响超乎想象。我的手机被打爆了,
有捐款的,有提供各种线索的,更多的是来安慰我的。肖然成了我的盟友,
她几乎每天都来,帮我整理线索,分析案情,比警察还要上心。一天,她兴奋地跑来找我。
周老师!有新线索了!有个目击者联系了我们,他说当晚看到一辆白色的轿车开得飞快,
虽然没看清车牌,但车型和嫂子的车很像!我的心猛地一沉。是吗……我挤出笑容,
那太好了!对啊!我们把这条线索告诉警方了,他们说会重点排查这个方向!
肖然握着拳头,为正义即将到来而激动。我却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。排查,
很快就会排查到我家里来。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我开始假装积极地配合肖然。
我打印了几百份寻车启事,上面印着那款白色轿车的网络图片。我和肖然一起,
在小区、在附近的街道,一张一张地张贴。有路人认出我,停下来安慰我,
骂着那个天杀的司机。我低着头,说着谢谢,感觉自己像个无耻的小丑。
肖然甚至安排了一次直播。在事故发生的那个路口,她把话筒递给我,
问我想对肇事者说些什么。我看着镜头,背后是车来车往的马路。我酝酿了很久的情绪,
然后用沙哑的声音,一字一顿地说:我不管你是谁,你为什么要逃。我只求你,
看一看我儿子的照片,他才七岁……我求你站出来,给你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,
也给我们家一个交代。说到最后,我情难自已,蹲在地上,掩面痛哭。
直播间里群情激奋,弹幕刷满了严惩凶手。肖然走过来,轻轻拍着我的背,
低声说:周老师,别难过,我们都在。正义不会缺席的。我蹲在地上,
在无人看见的阴影里,嘴角勾起一丝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冷笑。正义会不会缺席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,一场更大的风暴,正因为我的这场完美表演,加速向我们这个家袭来。
警方的排查通知,很快就要贴到我们小区的公告栏上了。5夜深人静,我像个贼一样,
溜进了自家的车库。我发动汽车,不敢开车灯,借着手机微弱的光,
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出小区。我不能去熟悉的修理厂,那太容易被查到。我凭着记忆,
把车开到了城市另一端的城中村。那里鱼龙混杂,遍布着各种没有正规执照的黑店。
我在一条漆黑的小巷里找到了一家挂着钣金喷漆招牌的铺子。老板是个光头,满身油污,
正在吃泡面。他打量了我一眼,又看了看我的车。撞了?嗯。我压低了声音,
想整个修一下,再换个颜色。老板吸溜了一口面,放下碗,绕着车走了一圈,
在那处破损的地方敲了敲。把车子颜色再暗一点,颜色变动不要太大,
最好不用我换行车本照片那种。我递上一沓现金,越快越好,钱不是问题。
老板接过钱,数了数,咧嘴一笑,露出满口黄牙。行,你明早来取。那一夜,
我没有回家,在一家24小时快餐店里坐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一早,我取回了车。它焕然一新,
变成了低调的银灰色,那处致命的伤口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把它停回了车库。做完这一切,
我才松了口气。可我没想到,我的这个举动,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
警方的排查开始了。很快,小区里另一辆白色同款轿车的车主,被列为了重点怀疑对象。
他姓王,就住我们隔壁一栋楼。是个程序员,性格孤僻,深居简出,
平日里和邻居们几乎没有交流。最关键的是,他的车身上,有几处陈旧的刮痕。
在那些被正义感冲昏头脑的热心邻居和网友眼里,这些刮痕,就是铁证。
肖然第一时间来找我。周老师,警察怀疑是老王干的!您见过他吗?他那个人怎么样?
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兴奋,像是猎人终于发现了猎物的踪迹。我沉默了。我知道,
只要我说一句不清楚,或者他看起来不像那种人,就能把嫌疑从他身上引开。可是,
如果不是他,警察就会继续查下去。我的家,我的妻子,就会暴露在危险之中。
我看着肖然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,她需要一个凶手来完成她的英雄故事。而我,
也需要一个凶手来终结我的噩梦。我深吸一口气,
用一种非常不确定的、犹豫的语气说:我……我不知道是不是他。我停顿了一下,
这是表演的关键。然后,我接着说:不过……他那个人,平时确实……怎么说呢,
不太合群。我们住一个小区这么久,几乎没见他跟谁打过招呼。这句话,
像一句淬了毒的判词。我没有指控他,但我把刀递给了别人。肖然的眼睛亮了。
她在我这句模棱两可的话里,找到了她想要的答案。我明白了,周老师。她匆匆离去,
一篇关于孤僻邻居成头号嫌疑人的报道,很快就要出炉了。我关上门,靠在门上,
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:我,正在亲手把一个无辜的人,推向深渊。6肖然的笔,
比我想象的更锋利。她的报道一出来,老王的人生就被彻底改写了。嫌疑人锁定!
孤僻邻居为何三缄其口?这样耸动的标题,像病毒一样在城市的朋友圈里扩散。文章里,
我的那句不太合群,被巧妙地渲染成一种反社会人格的佐证。
而老王车身上那些陈旧的刮痕,则成了做贼心虚,企图掩盖的铁证。评论区里,
一片喊打喊杀。很快,老王的个人信息被人肉了出来。
他的姓名、照片、工作单位、家庭住址,被毫无保留地曝光在网络上。
他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,只等着被钉在耻辱柱上。我开始在小区的业主群里,
看到邻居们拍摄的视频。有人用油漆在老王家门上喷了杀人凶手四个大字。
有人往他家窗户上扔鸡蛋和垃圾。甚至有几个情绪激动的年轻人,堵在他家门口,
指着他的鼻子辱骂,要他滚出来给周老师的儿子偿命。视频里,老王穿着一件旧背心,
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,他想辩解,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潮水般的咒骂里。
他那副老实巴交、不知所措的样子,像极了我在课堂上讲过的闰土。我关掉手机,
感到一阵反胃。我知道,这一切的源头,是我那句看似无心的话。我以为事情会就此平息,
警察会带走老王,我会得到安宁。但我低估了一个父亲的愤怒,也高估了自己内心的承受力。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,门铃响了。我打开门,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站在门口。她穿着校服,
眼睛又红又肿,手里紧紧攥着书包带子。是老王的女儿。周老师……她开口,声音沙哑,
带着哭腔。我心里一紧,下意识地想关门。周老师,求求您!她像是看穿了我的意图,
急得快要哭出来,求求您,帮我爸澄清一下吧!他不是凶手!那几道刮痕,
是半年前我不小心蹭到的,我们都有记录的!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。
现在……现在我爸被单位停职了,我走在学校里,所有人都指指点点……周老师,
您也是老师,您知道那种感觉吗?求求您,您去跟那个记者说一声,我爸他真的是无辜的!
她看着我,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和最后一丝希望。我看着她,就像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里,
走投无路、为父奔走的自己。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,疼得无法呼吸。我张了张嘴,
想说对不起。但我的身后,是同样在崩溃边缘的李月,
是还在ICU里等着救命钱的小远。我不能。我深吸一口气,
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:我……帮不了你。女孩眼里的光,瞬间熄灭了。
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,仿佛在看一个怪物。她没有再哭,也没有再求我,
只是那样死死地看着我,眼神里没有了恳求,只剩下一种我看不懂的、冰冷的失望。然后,
她转身跑开了。我关上门,背抵着门板,双腿发软。7老王女儿那冰冷的眼神,
成了压垮李月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天晚上,她把自己灌得烂醉。我回到家时,
闻到满屋子刺鼻的酒气。李月倒在沙发上,头发散乱,脸上挂着泪痕,
手里还攥着一个空酒瓶。小远……我的小远……她喃喃自语,像在梦魇里挣扎。
我走过去,想扶她起来。她却猛地推开我,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疯狂和恨意。
周峰!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!为什么!她嘶吼着,把手边的东西胡乱地朝我砸过来。